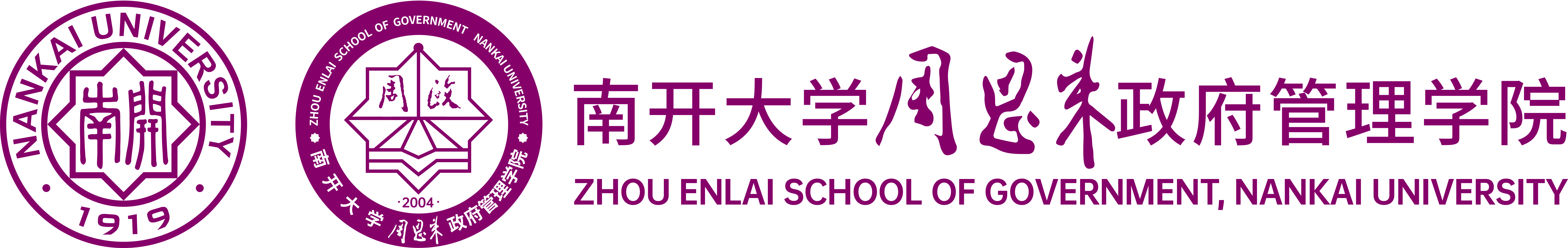城市是复杂巨系统,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安全风险,新兴风险与传统风险叠加,极易形成关联性强的灾害事故,严重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
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关注看得见的“地上城”的各类风险,对于看不见的“地下城”安全风险所知甚少;相应的安全治理存在“事后应急”的滞后性、被动性;应急管理过程中存在部门协同的困境;等等。
随着人们对安全风险认识的提高,中国城市的安全治理已经转向“大安全大应急”的部署。所谓“大安全”,指的是安全治理内容的全面化、系统化;所谓“大应急”,则强调面向安全风险的跨部门协调、“监测—预防—预警—处置—恢复”的全过程贯通。
“大安全大应急”体系的建设,单靠人工操作困难重重且难以为继。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大安全大应急”体系建设提供了支撑,使得城市的各类部件、要素可以“一屏展现”,应急响应联动可以“一键通达”。
这样一来,城市风险防控的种种问题,仿佛一经引入数字技术就可迎刃而解了。
但哪有那么简单!
数字技术的引入和应用并非建立在“无人区”,让它自运转就可高枕无忧了。如果人们真这样想,那就是“技术决定论”、患了“技术幼稚病”。这样的想法在实践和研究中还真不少。
实际上,离开技术万万不行,单赖技术也万万不能。数字技术的引入需要正式组织体系的评估、认可和调适,数字平台的建设需要公共组织和非公共组织的合作,数字技术的应用更是高度依赖组织之间的联动。所以,不考察技术与组织的关系,就不能理解数字化转型本身。进一步来说,组织关系才是数字化转型的命门所在。那么,什么样的组织关系才能利于数字化转型呢?也是本书最终要解答的问题。
讲到这儿,或许有人会提出了,不是已经有成形的“技术组织互构论”了吗?那我可以继续追问,技术组织是如何互构的呢?二者何以互构呢?技术再怎么发展,也需要组织来检阅和使用吧,那么,组织的态度如何、组织怎样接受和适配技术、怎样驾驭和使用技术呢?看看,这样一些打破“界面”、深入其中的关键问题,总是那么容易被人忽略。
一 从“城市性”讲起,给城市风险画象
从有历史记载以来,人类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对城市有着这么多的依赖和寄托。人们日益集中到城市中来生活了,“地球村”已然变成了一个“地球城”。由于现代信息技术、交通技术的发展进步,生活在城市的人们沟通交流更加便捷,“地球城”甚至成了“地球社区”。
人们尽管在城市里繁衍、生活、工作、交往、做美梦以及焦虑,却对生死相依的城市所知甚少。我们的城市是什么?是海棠花开春风里的风景,还是在晨曦中推门而入的职场空间?是上下班拥挤堵塞的路途,还是一抹能治愈人心的晚霞……看吧,多少种答案。但是,我们就是无意、不愿、不忍去顾及,那些脱轨脱缰的、洪水猛兽的、肆虐暴戾的城市“阴暗面”。
殊不知,我们无意、不愿、不忍去思索的“阴暗面”,也是城市的一部分。所以,我说要做好城市治理,首先要理解“城市性”。城市肯定不只有“积极的一面”,还有它“消极的一面”。那些“消极的一面”,就是要去监测、预防和控制的风险,这也是推进城市安全治理的基础。
因为本书讨论的是城市安全治理,所以就从城市风险的认知和理解开篇了。
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速,安全生产事故、社会安全事件陆续成为城市安全治理的重点。当前,城市主要面临“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居住安全、能源安全、金融经济及网络安全”等8类风险。因为城市人口密布、部件密集,事故灾难一旦发生,很容易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毁、环境污染等关联灾害,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危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城镇化进程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截至2024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7%,全国设市城市城区总面积11.02万平方千米,实际建设区域7.80万平方千米,城镇常住人口达到9.435亿人。
在城市地上,高楼林立、人口聚集、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在城市地下,广布着人们看不见的水利、电力、天然气、热力、交通等基础设施,它们被称为“城市生命线”。截至2024年,全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的总长度达10945.6公里,城市的供水管道长度达110.30万公里,排水管道长度91.35万公里,天然气管道长度98.04万公里,供热管道长度49.34万公里。
在很长一段时期,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设与管理中“重地上、轻地下”,“地下城”的发展与安全往往不易为人察觉,难以受到重视。与此同时,早期工程设计相对保守、前瞻性不足,各种管线密如蛛网,地下空间功能布局杂乱,部分地下管线“超期服役”,性能老化问题日益凸显,“地下城”的安全风险一再累积、频频爆发,“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事件时有发生。
“地上城”与“地下城”是城市的“表与里”。那么,“地上城”和“地下城”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风险?这些风险是微弱可略的,还是可能演化放大的?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些风险才会被人所知所感,形成令人恐惧的灾害危机?
本书的上篇主要就是给特大城市的风险及其演化画象,给出一得之见。
二 引入数字技术,展开“数字算法”的畅想
人力所不及,算力多神奇。
“大安全大应急”已成为城市安全治理的主要思路。新组建的应急管理部将原来分散的自然灾害类和安全生产类应急职能进行了系统整合,是对管理对象、管理职责、管理过程的高度统一。应急管理体系也从过去单一灾种应急向综合防控转变。
那么,特大城市风险防控的现实情况是怎样的?面临什么样的困境?
在我们国家的体制内,城市政府的风险防控是一项“政治性强”和“刚性约束强”的工作。安全往往被强调是一种“底线”,也是一条“红线”。城市政府的安全治理工作已经从原来政府主责变成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但是,城市的安全治理还面临着“风险底数不清、属地责任约束、基层权责失配、防控衔接难题、协同联动困境”等等工作短板。怎么办?面对“大安全大应急”新发展要求和现实工作的困境,数字技术仿佛一把利器,劈开了风险防控的迷雾,让城市主政者得以窥见数字化的曙光。
中国城市的风险治理正经历着从“分散应急”向“大安全大应急”的跃迁。数字技术的引入,给“地上、地下两座城”配备了千里眼、顺风耳。一座基于数字技术的“云上城”,能够实现城市“状态感知、建模分析、城市运行、应急指挥”,从而提升城市整体的安全性与韧性。
这种转型不仅体现为应急管理部的机构整合与职能重构,也更深层次地反映着风险认知范式的革新:安全治理的范畴突破物理空间的“地上-地下”区分,向着全域感知、全要素联动的立体防控网络演进;应急管理的过程超越“事后响应”的被动模式,形成“监测-预警-处置-学习”的韧性治理闭环。数字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重构城市安全治理的底层逻辑——通过亿级物联网终端的全域感知、城市信息模型的精准映射、智能算法的超前预警,数字技术似乎为破解“黑天鹅”“灰犀牛”交织的困局提供了可能。
人们对于数字化的畅想泛滥而高亢。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各地是如何操作的呢?
我们先用大数据分析的方法对全国特大城市的数字化风险防控摸了一个底。结果发现,在技术条件相对较好的大城市,数字技术应用的环节、范围与理想所期还有一段距离。显然,问题在不数字技术不能用,而在“组织是否适配”。这就排除了“技术决定论”,也对“技术组织互构论”打了一个问号。到底怎么互构呢?什么样的互构是有效的呢?
那就走向实践,让实践说话。本书第二篇就是对“数字技术之用”的初步解答。这个初步的解答,犹如一簇星火,撩拨起探索的心弦。笔者带着团队到了10多座特大城市调研,这些城市各有各的做法,各有各的逻辑。为什么这些数字技术基础不错的城市,数字化风险防控的态度、实践效果不同呢?奥秘在哪儿?
通过对特大城市数字化风险防控的深度解剖,我们发现,当数字技术嵌入中国特色的组织体系时,既有的“条块关系”“科层体系”“政企社关系”等组织逻辑正在发生着深刻嬗变。数据整合的实质是部门权力的再分配,算法应用的深处是组织关系的重构。这些发现不仅挑战着“技术组织互构”框架,更揭示了数字化转型的独特路径——技术赋能的有效性始终受限于组织变革的彻底性,而组织变革的深度又反过来塑造着技术应用的边界。这就是技术的组织建构论,也即,
技术并非数字化转型的充要条件,决定数字化效果的乃是组织建构。
所以,本书的核心主题不是去给混沌的“技术组织互构”之火添薪加柴,而是从组织学的角度来解释数字化转型。
三 打破技术“乌托邦”,寻找数字化转型的“组织密码”
当特大城市将风险防控的愿景寄托于数字技术时,技术乌托邦的想象往往掩盖了更深层的组织逻辑。当前实践揭示的悖论在于,城市遍布了各种传感器,风险预警和响应的效率却并未形成正向关联,数据平台的算法转变加剧了部门的成本负担和部门间的博弈。这迫使研究者必须直面数字化转型中最具挑战性的命题——当数字技术遭遇科层组织固有的运行逻辑时,究竟何种组织变革能够释放数字治理的效能?打开这个“黑箱”的钥匙,不在数字技术这里,而在于组织。
本书第三篇试图通过三个关键问题的解构,揭示特大城市风险防控数字化转型的组织密码。
第一,数据整合何以突破组织壁垒?在数字化转型的蓝图中,跨部门数据共享被预设为技术赋能的自然结果。仿佛上级一声号令,即可一呼百应、一气呵成。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现实运作中,各个部门的信息存在交互屏障,有的部门还在前信息化时代,有的部门不愿意分享数据以免“暴露家底”“暴露短板”被相关部门问责,有的部门则担心由此带来各种成本。这种种矛盾折射出一个深层的组织学命题:当数据资源成为新型治理资本,科层体系内部如何重构数字权力的分配规则?各部门对数据控制权的策略性保留,不仅源于技术标准的差异,更是对组织权威再分配的防御性反应。破解“数据烟囱”困局的关键,在于重构数据流动背后的激励机制与责任框架。
第二,技术治理的可持续性何以维系?物联网设备指数级增长背后,隐藏着治理模式的结构性张力。对于一座智慧城市运行而言,物联智能感知设备已成为城市运行数据全面感知、自动采集的有效手段。但是,这些设备、系统的投入巨大,后续还会面临运维和迭代升级的压力。可以讲,数字化风险防控是一件很“烧钱”的事情。青岛市在市内三区新建智能感知设备近万台,对主城区城市生命线工程安全、公共安全领域的风险监测,投资2.04亿元。若以此测算推广至全市,仅此项设备投入就要接近10亿元。深圳市仅在城市生命线工程安全建设总投资就达50.25亿。未来,城市数据收集的布设点位越来越多,相关物联设备的投资建设、运营维护、数据采集和运算的可持续,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一些城市的数字化感知体系的运营维护费用,短期内就可能超过初始投资数倍。这种“数字沉没成本”现象折射出技术治理的单向度思维困境:地方闷着头上设备,但是成本到底由哪个部门来承担?当设备更新速度超越组织适应能力,当数据洪流冲破既有组织承载边界,数字技术反而可能成为组织失能的催化剂。
第三,组织联动的制度密码何以破译?城市安全治理不能毕其功于数字平台建设一役。大数据的应用能否得到组织协调的响应,是其在风险防控中发挥作用的关键。已有的一些突发事件表明:风险源虽然已被技术实时监测到,相关行业单位已明确发出预警,但由于部门联动的滞后,导致风险放大、级联灾害升级。可见,“技术组织互构论”并非一个简易的“自动装置”,二者的互动也不能止于“界面式”的抽象想象。数字化风险防控真正的密码,藏于组织联动之中。
数字化风险防控,是多层级(市-区-街-居)、多部门(综合管理部门、行业监管部门、业务权属部门)、多主体(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社会和公众)等的协同活动。诸多的案例分析揭示,应急响应延迟或失效的主要原因在于跨组织联动的失灵,而非技术系统的物理障碍。这昭示着“技术组织互构论”存在结构性盲区:在数字界面联通的表象下,科层组织的决策惯性、责任边界与激励约束结构仍在支配着数字技术的实现程度。当应急指挥体系遭遇部门权责的“数字黑箱”,技术赋权可能加剧组织博弈的复杂性。
这些问题共同指向数字化转型中未被充分理论化的核心维度——组织关系的重构。
本书试图超越“技术决定论”与“技术组织互构论”,在技术装置与组织架构的互动场域中,揭示特大城市数字化风险防控的组织建构逻辑。
通过解剖中国特大城市的数字化转型实践,本书将展现:当技术革新遭遇组织惯性时,那些看似技术瓶颈的治理困境,实质都是组织逻辑在数字空间的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