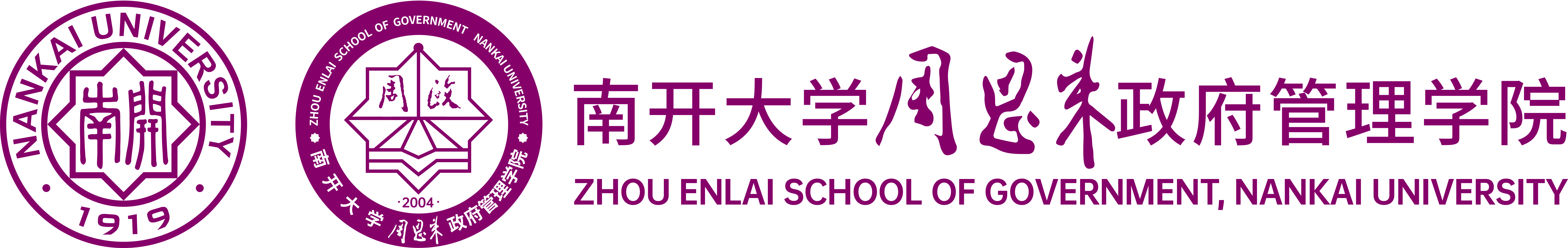《时代周报》特约记者 温墨 刘慕鑫
2013年3月10日,全国“两会”第八天,中国第七轮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大幕正式开启。坊间流传的撤铁道部的消息被证实,同时被证实的还有国家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合并的消息,始自10年前的“大部制”概念如今一步步渗入到中国政治生活领域。那么最初的“大部制”指的是什么?当初的改革设想和如今实行的是不是一回事?如何看待目前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作为“大部制”概念的提出者、大部制改革方案最早的研究者之一,南开大学副校长、著名政治学家朱光磊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叫“大部门体制改革”更准确
时代周报:两会召开,很多人对“大部制”改革充满了期待,作为研究中国政府过程的政治学家,你对“大部制改革”的理解是什么?
朱光磊:应当注意,从第一轮大部制改革来看,标准词汇是“大部门体制改革”。学者最初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包括我自己,所使用的大多是“大部制”。“大部制”和“大部门体制改革”含义基本相同,但还是有细微的区别。而且,我认为,有关细微的区别应当给予关注。
第一,“大部门”显然大于“大部”。从横向范围来看,“大部”强调的是部(委)与部(委)的整合、归并;“大部门”除了强调国务院的各部委之外,还应包括国务院的直属机构、办事机构、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和事业单位,乃至党群口的部门。同时,“大部门”和“大部”还有纵向层次上的区别,“大部”仅指部(委)本身,我觉得“大部门”还应包括各部(委)的内设机构,比如说司、局、处之间的整合。
第二,加了“体制”,改革的高度就出来了。只讲“大部制”,往往谈不到改革,两个部门合成一个部门就可以叫“大部制”,而“大部门体制改革”的含义显然就复杂多了。这一点值得党政机关和学术界的朋友们注意,不要一说“大部门体制改革”就只是想着合并部委。
也就是说,“大部门体制改革”就是指把相同或相近的政府职责加以整合,归入一个部门为主管理,有关部门协调配合,或是把职责相同或相近的机构归并成一个较大的部门,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责交叉、多头管理和部门主义,从而提高行政效率,而不仅仅是部委合并。
“大部门体制”?
时代周报:据我们所知,其实在很早之前,你就做过大部制改革方面的研究工作,2004年就提交过设计“大部制”的研究报告给中央有关部门。
朱光磊:2004年,我的研究团队通过中央编办提交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研究报告,当时我们用的就是“大部制”。但是,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叫“大部门体制改革”,我很认同,比我们提的“大部制”更好。我们主要是从推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理念来提出诸如此类的建议的,而不是对机构和编制的简单裁撤、削减。我坦率地说,中国的公务员队伍在整体上是不错的,他们面临的压力很大,他们中的大多数工作很辛苦,我们国家的改革、发展和稳定,都离不开他们的劳动。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存在的毛病,主要不是出在一个个的个体的身上,而是出在了“衙门”和“图章”上,—做事情,就得去“衙门”,就要“盖章”,所以,最好“衙门”少点儿,让老百姓和企业少盖点儿章。当时的想法要比现在简单。
2004年前后,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提出了这个事情。当时,我们和中央编办有着长期的合作研究关系。中央编办对我们也很信任,比较认可我们的工作。挂靠中央编办的中国机构编制管理研究会的成立和年度课题工作的启动,使我们团队与中央编办的工作联系实现了常态化。目前,我的研究团队还有孙涛、贾义猛等学者,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而且做得很好。
时代周报:你认为,2008年启动“大部制”改革的原因是什么?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朱光磊: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政府部门总体上比较多,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最多曾达到过100个(含办事机构等)。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居然还出现过一些用产品(商品)的名称来命名的部委,例如机械部、煤炭工业部、纺织部等。
改革开放以后,经过几次调整,特别是经过1988年、1998年几次调整,通过总结几轮循环的经验教训,开始从政府职能转变的角度考虑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央政府部门,到2008年大部门体制改革的时候,国务院组成部门已经是不到30个了。
我们中国人其实特别注意国外的情况,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情况,有一部分朋友甚至是看到外国的情况,往往总是先从好的方面去想,对国内的情况,往往是先从负面去想。这种思维方式固然有些问题,但也有助于促使我们发展得快一些。就机构编制问题看,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家,一般不超过20个,15个左右的国家也不少。几个引人注目的新兴国家,在20—30个之间,和我国差不多。这是外在压力。
显而易见,到21世纪初,与国外相比,我国中央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数量差别已不大。差别较大的主要是两块,一个是政法口、文教口;一个是具有中国特殊性的部门,例如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民委等。此外,实事求是地说,党群口也有一些需要整合的部门。
所以,实际上,从国内的情况看,大家关注、支持实行“大部门体制改革”主要是基于转变政府职能,减少部门数量的角度考虑。当然,和外国相比,我们的部门数量还是多,也是重要原因。也就是说,最初的改革动因,是内部外部两个方面的合力。这一改革的要求是合理的,是合乎政府发展的基本规律的。
中央机构再压缩余地不大
时代周报:对于如何摆脱传统计划体制,当时有什么构想?是否有明确的改革目标,还是后来慢慢形成的?为何大部制改革到了2008年才启动?
朱光磊:国务院组成部门从50-60个,减少到不到30个,中国用的时间应当说不是特别长。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有惯性的,马上做调整,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到位的。我们对政府职能转变的速度不是很满意。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也不能完全否定1988年以来,特别是1993年以来,在转变政府职能时所做的大量工作。比如,我刚才谈到的那些按照产品命名的机构,不是早都精简掉了吗?
还有我国政府各大职能部门的组成,一般有这样一个规律,就是分为综合部门和业务部门两大块,过去业务部门往往是负责直接管理企业的。在改革过程中,首先,按产品设置政府部门没有了;此后,部门内设业务部门所管理的企业,随着国资委的设立,也陆续剥离了。这两大块的精简,不含糊,而且社会没有因此出现大的动荡,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一方面,我对政府职能转变迟迟不能够基本到位,作为一名学者,感到着急;另外一方面,公允地讲,也要看到几次改革和精简,幅度不小,变化很大,做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不能够轻易地否定。
1993年,中国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时期。1993—2008年,15年,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大部制改革提上议程,我不能说它早,但我也不能说它很慢。从2008-2013年,又是5年时间,有人问,为什么中间没有抓紧进行新的改革。我认为,政府机构的调整,应该是有周期的,不能天天调整,—天天调整,改革的态度是好的,但恐怕也不严肃。
谈到这里,我想说一下,中央政府的机构数再往下压,余地已经不太大了。如果我们把机构数压缩到14个,像有的国家那样,还是有困难的。是不是有这个必要?值得推敲。比如日本的文部科学省,大体相当于我们的教育部、科技部、文化部,但如果我们把教育、科技管理、文化事务等政府职责归并给一个部,恐怕是会有一些副作用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政府管得偏多,传统上就是一个“行政导向”很强的国家,在这样的政治背景和行政文化氛围的条件下,再加上人口和地域的因素,我们的政府部门不大可能太少。所以,如果本次人大会议能够再推出几个个案,就是一个比较满意的情况了。今后的关键是深化。
政府机构怎么设置都会有空当
时代周报:你在《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一书中提出这样的观点:“作为多年来对机制完善问题重视不够的一个具体表现是,我们还较少从政府过程的角度分析政府现象。”你提出大部制改革建议与此有关吗?
朱光磊:一方面,中国政府发展的程度还不是非常高,另外一方面,我们整个社会对中国政府发展的要求却又相当高。我不主张对体制、机构的调整过于频繁。有问题,就先带着问题去运行,—反复观察,看准了再下手。对行政体制和政府机构的改革,应当是以十年为一个周期,至少要以五年为一个小周期。一个国家,如果天天在改体制、改机构,我觉得,这和僵化相比,是另外一个方向上的问题,也不好。我们不能僵化,但是机构的改革,体制的改革,要有稳定性,要有阶段性,要给人喘气的机会,要给人思考的余地,而且要避免不必要的反复。问题总是有的,不存在没有问题的时候。从哲学的角度讲,任何机构,总是带着问题运行的。
第二,对机制的研究不够。行政体制改革实际上包括体制和机制两个方面,但是目前分析问题的时候,精力基本局限在体制层面。所以才有了刚才提到的问题,天天谈体制改革,人人谈体制改革。实际上,通常说“九龙治水”的问题,“相互推诿”的问题,有体制的问题,也有机制的问题。有的问题,是需要通过部门协调来解决的,而不一定非要通过机构的增减来解决。任何时候,一个国家的政府机构,都不可能覆盖其应该做的所有事情,怎么设置也会存在空当。另外一个就是,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各个政府机构所承担的职责,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互不交叉。一方面就是说,不会百分之百的覆盖,另一方面,在某些问题上,又可能出现职责重叠。世界上的好多事情,是复杂的,是很难划清彼此之间的界限的,要求政府机构的职责划分有绝对明确的界限,那是不合理要求。似乎高层对这些事情并没有真想清楚,对下级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必须要实事求是地考虑这个事情。
但是,我绝不是说要无所作为。我是说,凡是这样的问题,往往是需要用机制调整去平衡体制改革。机制的调整,是可以经常进行的,新机制运行不理想,还可以很快再进行调整,甚至退回来;体制改革就不同了,一旦动了“手术”,就不容易在短时间内再做调整,因此体制改革我主张应当是分阶段、有重点的。凡是能通过调整机制解决的问题,就先不要动体制。不动,不是绝对不动,而是留在以后再进行调整。在此类问题上,我们既要积极,又要稳健,免得走回头路。
中国人想事情往往太急
时代周报:你对从2008年开始组建的工信部、人社部、环保部、住建部、交通部的大部制调整结果如何评价?成绩是什么,还有哪些问题?难点在哪里,原因是什么?
朱光磊:总体上是积极的。现在有一个说法,比如说两个机构合并,两个大学合并,人们就说,十年也磨合不好。而我认为,十年能磨合好就不错,就值。中国人想事情往往太急,以个人生涯的长度来思考改革进程,只要是自己赶不上了的事情,就觉得太慢了。
部委合并之后,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出现运行方面的问题。如果铁路合并进来,会不会在短时间内完全到位,我看是有困难的。如果10年可以到位,个人认为,可以接受。甚至就不要追求一步到位,因为长期是分开运作的,要求一步到位,简直不敢想象。这样的事情,宁可慢一些,先做起来就好。我对2008年的大部门体制改革,按照我现在掌握的信息,是给予积极评价的。
时代周报:此前广为流传的“大能源”、“大文化”、“大金融”、“大体改委”等部门的改革,暂未列入此轮“大部制”改革的重点。
朱光磊:我觉得这是需要分步骤操作的,而且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机构数越少越好和机构单体越大越好的问题。
政府职能转变是枢纽
时代周报:你觉得“大部制改革”,或者说国家行政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在整个行政改革、政治改革中到底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公众对此可以有何种期待?
朱光磊:要区分两个问题,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这是两个密切联系,但又有着很大区别的任务。政府职能转变是一个大问题,一个基础性的问题。我特别重视政府职能的转变,呼吁中央对政府职能的转变要给予比现在更大的关注,—尽管现在已经很重视了。政府职能转变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结合部”,同时又是行政体制改革、机构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和壮大社会组织等一系列重要改革的基础。
“政府职能转变”是个政治学的概念,但这个政治学的概念,是1982—1986年期间,由经济学界的朋友们最早提出来的。当时,企业改革开始提上日程,为此不谈转变政府职能是不行的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是从政治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恐怕很难,有些人会有疑虑的。从社会运作的角度看,这既是个政治问题,又是个经济问题。中国的政府职能实际转变的程度,同时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实际进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我呼吁高层对政府职能转变问题给予比现在更大的关注,做更加系统的研究。
转变政府职能的问题不仅仅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它也是政府和社会的关系问题,还涉及纵向间政府关系的问题,—我不主张简单地叫中央和地方关系,因为如果叫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最后说来说去就变成了中央和省的关系,而中国省及以下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也相当复杂,需要解决的相关问题很多。如果政府不转变职能,我刚才罗列的几项重要工作都不可能完全到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从项目上说,显然国家各个重要政治要素之间的关系的调整是最基本的任务,其中的“党政关系”是最核心的东西,但在大家一时达不成共识或操作条件一时还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我们把转变政府职能做一个枢纽,作为连接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枢纽,我觉得是一个合理、现实的选择。
那么,在转变政府职能的问题上,我想专门说一个问题,也是我第一次谈这个问题,就是呼吁我们大家要坦然接受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给社会生活基本面带来的变化。我们不能只是愿意接受我们比较好接受的东西,而不愿意接受我们比较难接受的东西。这也是转变政府职能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比较好接受的方面,这是大家都熟悉的一些工作,也是这几年我们大家都做了的,但是还有一些我们不是太好接受的。比如,对有些事情,我们是否要敢于说我们的政府管不了,也不想管了!要敢于这么说。我们现在是一方面说我们政府要缩小活动的空间,一方面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我都听不到有政府人士说,某某事情,执政党和政府不能管,单位也不宜管,你自己负责,如果有争议,我们就依法办理。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做到。这些事情的出现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对政府职能的问题并没有真正想清楚,二是没有坦然地接受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对政府职能所提出的要求。只是接受了一部分,有一部分是采取了回避的、拖的态度,实质上还是习惯于或者是内心里还是愿意多管一些。我们社会当中的很多问题,包括“维稳成本”等方面出现的一些需要商榷的问题,大多与此密切相关,而这些问题是通过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所解决不了的,甚至是调整了“党政关系”也解决不了的。它牵扯到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怎么看待政治,怎么看待行政,怎么看待国家和政府?对这些问题的理论研究要加强。
警惕部门滥权
时代周报: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大部制固然是为了理顺体制,提高行政效率,但另外一方面,部委权限大了之后,如何保证不滥权?
朱光磊:滥权的问题也正是我所担忧的事情。这个事情的解决,还要从转变政府职能上来考虑,还是从政治体制改革上来考虑,机构调整本身,小修小补,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在这个基础上,我谈一谈大部门体制改革深化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提出的基本观点就是:
第一,大部门体制改革有必要从政府扩展到党群口,不要只做政府的文章。党群口中诸如有些调研、培训类的机构,应该进行整合,不然的话,资源就浪费了。
第二,隶属党政机关的有些研究、咨询、培训机构,可以采取和高校、科研院所共建的方式。成本低,而且还有弹性。比如国外有些著名大学的研究所,实际上就是隐性的政府部门,政府出钱,编制和经费也是单独的,它们的调研报告等,往往是以高校的名义抛出,看社会的反应,它们是可以给政府做很多事的。党政机关不必事事亲为,特别是一些调研、培训工作,不一定要设很多专门机构,有些工作宜采取共建的办法,采取有实有虚的办法。
第三,是我特别强调的,要加强部门内设机构的大部门体制改革,我建议今后十年把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内设机构的调整作为大部门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引导着大部门体制改革向深度发展。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内设机构过细。我的看法是,“部门要少,人员要饱满”,我不赞成“用人越少越好”的思路,用人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要适度。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条件下,在整体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大背景下,简单地强调一压再压,不现实。比如最近我的研究团队到广东的一个市辖区去调研,发现这个区的户籍人口30多万,但是常住人口加上流动人口是300万左右,而它的机构编制还是1996年确定的,它怎么运作,怎么能运作得好?它要是运作得好,就得采取非常规用人方式。不要总讲唐朝用多少人,第一,是否有充分的档案我都表示很怀疑;第二是情况完全不同。我们常说有些国家的政府机构只有十几个,但那是指“内阁级机构”,非内阁级的机构和临时机构也是大量存在的。
第四,要在这些包括大部门体制改革在内的体制改革的同时,建议高层进一步强化机制建设,特别是要注意解决好“部门协调”问题,要总结中国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诸如此类的做法和经验教训,发挥其好的方面,避免其不利的方面,在机制上做文章。我团队的周望博士对此就很有研究。
最后,实际上中国在这些领域当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目前还没有实质性涉及“官本位”问题。中国到了解决“官本位”问题的时候了。改革开放30多年这个问题如果还不着手解决,将来在历史上讲不过去,由此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带来的负面作用很大。中国现在是几乎“人必称级”,导致我们的政治文化不够健康,而且在技术操作上作茧自缚。比如,一个镇的人口规模发展到了一个中等城市的程度,它现在也难以设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难在县级市之外再搞个“镇级市”。实际上,如果我们淡化了“级”的概念,“市”就是“市”,这就不是个问题了。我们要跳出思维惯性,我们现在的行政区划改革之所以步履艰难,就是不断地在平衡“级”的因素。如果压根就不把“级”放在现在这样的高度和广度上,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矛盾其实是自己设置出来的,我们要跳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