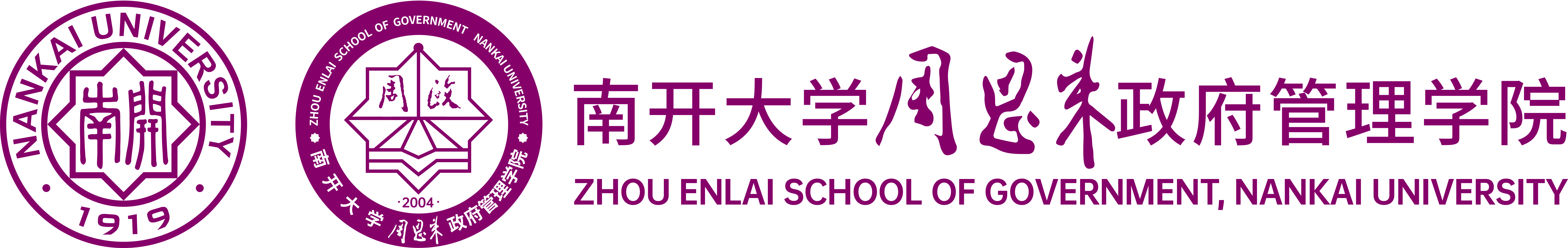昨天一大早就接到大洋彼岸传来的噩耗,我在伯克利加大读博时的导师,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大师肯尼思·沃尔兹与世长辞了。没有太大的震撼,甚至没有过多的悲恸,因为这是近年来自与他相依为命的老伴海伦仙逝后我一直在担心会发生的事;而且我一向认为,人到了这个年纪(近九十高龄),要走还是以快为好,我曾有过太多亲人在漫长病痛中备受煎熬折磨的经历,深知干脆利落地退场也是一种福分。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作为一代学术宗师,老人登上了人生事业辉煌的巅峰。如此的完美谢幕,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我能成为沃尔兹指导的“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获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沃尔兹语),并非事出偶然,而是我主动选择的结果。赴美读博的第一年我在奥斯汀德州大学,但第二年便转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不仅因为当年伯克利的政治学与哈佛并列全美第一,而且因为那里有两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领军人物:现实主义阵营的沃尔兹和自由主义阵营的厄恩斯特·哈斯同时在那里任教。有意思的是,这两位统帅纵有千军万马在各自麾下对垒拼杀,却在伯克利校园同一栋楼的同一条走廊中相距不到20米的两间办公室里分别安营扎寨,偶尔在走廊里撞见还绅士般地招呼致意。美国大学一般规定,同一课号的课即便是不同老师授课也不允许学生重修,但伯克利政治学系为这两位大师破例,允许研究生在修完一位大师讲授的“国际关系理论”课后再修一次同样课号同样课题却是不同大师讲授的课程。就这样,在这种“斗而不破”、“和平竞赛”的良好学术氛围中,我在沃尔兹的指导下花了九年时间才拿到了政治学的博士学位(攻读伯克利政治学博士平均费时8年半),这与他的高标准、严要求当然是分不开的。
沃尔兹在学术上对真知的追求和坚持几乎已经到了严苛的地步,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不同的学术观点抱有宽容的态度,尤其对学生,更是给予更多的空间任其自由发展,而不是硬把他们拘禁在某种思想藩篱之中。由于我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决策理论的关系方面与他有不同看法,起初他对我的博士论文的理论框架不予认可,但经过我们之间多轮往返的通讯讨论(他那时已经移师哥伦比亚大学),他终于承认我能做出自圆其说的辩护而予以通过。在“政治立场”上也是如此。我的论文对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霸权主义多有批评,有些批判甚至很尖锐,沃尔兹虽然很爱自己的国家,但从不护短,对于那些言之有据的批评给予完全的支持,还好心提醒我注意某些提法不要过于刺激,免得在论文通过时遇到麻烦。
沃尔兹不仅在纯学术的理论上独树一帜,创立了一个全新的学派,单枪匹马地改变了20世纪国际关系学科的面貌,而且在与现实紧密联系的外交政策分析方面极富远见卓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看问题不带西方或美国中心论的偏见。在谈到当年中国出兵朝鲜的问题时,他对我说,在当时美国大军进逼中国边境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大国都会像中国一样做出反应去维护自己的“安全缓冲区”。这种意见在美国是很另类的,因为多数美国人只承认美国有权保持“安全缓冲区”,却绝不承认别国也有同样的权利。
一般人对现实主义者抱有误解,以为他们只认本国利益并且只以实力论高下。作为当代现实主义第一人,沃尔兹在一生的政治立场上身体力行了现实主义“明智的利益”(承认别国的正当利益)和“审慎的权力”(切忌滥用权力)两条原则。当年越战期间,沃尔兹就是反战运动的舆论领袖之一;2003年美国发动侵伊战争前夕,沃尔兹和几十位重量级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在《纽约时报》刊登整版广告,反对这场战争。沃尔兹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反对这些战争的理由是在这些地方都不存在美国的重大利益,发动战争只能是武力的滥用,是“帝国的过度扩张”。
在伯克利,我和沃尔兹的交往局限于我在他的Office Hour(专门用于给学生答疑解难的时间)去他的办公室向他请教学习上的问题。直到2004年我请他来南开讲课,才有机会与他近距离接触。那时我在南开大学举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大师系列讲座”,请的第一位嘉宾就是我当年的导师沃尔兹。在南开的两周时间里,年届八十的老教授每天上午给本科生或研究生讲三节课,下午休息;但遇到与中国学者开会对话,就是一整天的日程。沃尔兹是由他的夫人海伦陪同来到南开的,就住在校园的专家楼里,生活简朴,工作认真。他的讲课特别受学生的欢迎,有的片段还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有一次给研究生做讲座,除了本校的还有很多外校来的研究生参加。一位北大女生提问:您的理论以国家求生存为前提预设,在当今的文明世界中,国家的生存难道还是问题吗?那天我是讲座主持人,就对那位同学说,伊拉克的例子就在眼前,怎么还会问这样的问题?但那个女同学并不买账,争辩说:伊拉克那个国家不是还在吗?不是已经成立了临时过渡政府吗?这时,沃尔兹笑眯眯地插进来说,“That's us.” (“那是我们”, 意指那个政府只是美国的傀儡。)
我们中国人讲受了师恩就要图报。能让我聊以自慰的是,那次请沃尔兹夫妇来南开,在接待上给予他们极高的礼遇。首先,我们通过向有关部门申报,为他们争取到贵宾待遇。此外,当时的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还专门为他举行仪式,授予他南开大学名誉教授的殊荣。沃尔兹在美国以外只接受过两座大学的名誉学位或教职,一是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另一座就是南开大学。
沃尔兹作为一代大师,声名远播,却十分平易近人,返璞归真。在专家楼住宿的两周时间里,都是在附设的餐厅里用餐。老夫妻两人吃得很简单,却有一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每次吃饭他们都用可笑的洋腔向服务员索要“辣油”!这是他们仅有的几个汉语词汇中最重要的一个。后来餐厅的服务员干脆给他们准备了一瓶辣油,每次吃饭不用开口就会送到桌上。沃尔兹不看电视、不用电脑,但他对国际新闻一天都不能落。我的一个学生给沃尔兹订了半个月的《国际先驱论坛报》(正好是沃尔兹点名要的报纸),这样就保证了他在南开期间对外信息渠道的畅通。对于他这样的文化人来说,这种精神食粮甚至比物质食粮还要重要。让我欣慰的是,由于我们的努力,这次访问成为沃尔兹历次访华行程中最令他和夫人高兴的一次。遗憾的是,它同时也成了他们对中国最后一次的访问。
张睿壮 南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转自 东方早报 http://www.dfdaily.com/html/51/2013/5/15/997062.shtml)